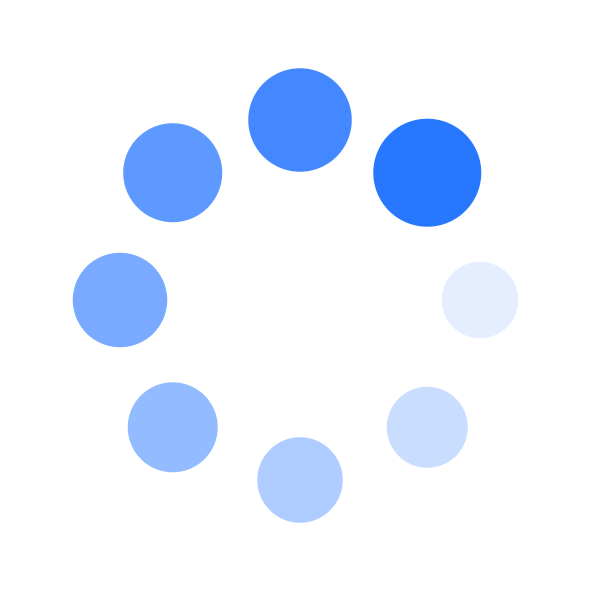静静的产院
茹志鹃
晚霞的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最后变成淡墨画似的几笔。公社产院外面的篱笆上,那些粉色的小花,也分不清朵数,形成模糊的一片,天色晚了。
谭婶婶挑满了一缸水,连气都没有歇一口,就忙着给两个休养的产妇做饭。在她这样的年纪,有这一份精力,这是她觉得自豪的。
在这里,在这所“跟医院差不多”的产院里,谭婶婶不但剪掉了发髻,她还学会了打针,打肌肉针、静脉针,学会了做产前检查,学会了量血压抽血、缝线、拆线。每每碰到一些小手术,请镇上医生来动手术的时候,她就从容容地做助手。对她的熟练沉着,医生也夸奖,甚至有的医生进一步要她自己学着动些小手术。谭婶婶笑笑,有些得意,同时这些医生把这产院要求得跟城里的医院一样,她又觉得好笑。谭婶婶对这一切都感到满意,不是没有道理的。
锅里的水嘶嘶地响了,谭婶婶心里翻腾了一阵,就望着电灯,恨不得立时来一个产妇,她真想在电灯光下面接生,就像在镇上,在城里的医院里一样:产妇躺在洁白的产床上,躺在雪亮的灯光下……
忽然啪的一声,电灯亮了,谭婶婶吓了一跳,回身一看,一个面孔黑黝黝的年轻姑娘,扛着行李,一手挟着一只氧气瓶,浑身热气腾腾地站在门口。
“婶婶,你不认识我啦!”那姑娘笑眯眯地站着没动。
“是二丫头!”谭婶婶跟二丫头的娘,还是做姑娘的时候就是好朋友,直到现在老姊妹俩还要好得很。
“婶婶,我派到这里来工作了。”荷妹回身坐下,就要谭婶婶介绍些产院的情况。
“其实,差不多的情况你也都知道。这产院负责附近两个大队的产妇。跟我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个周嫂嫂,现在她害喜(指妇女怀孕初期种种感觉不舒适的反应),回家休息去了。产院成立这两年里,我们一共接了三百五十六个宝宝,还都顺顺当当。”谭婶婶一说到这些问题,不由得话就多了。三百五十六个,这可不是容易的啊!这要担多少风险。特别是产院还没有条件自己动手术,很多情况就得当机立断。该请医生的就请医生,该送医院的就送医院,差一点点就会坏事,所以谭婶婶说到这里,特别加重了语气:
“二丫头,这可是一副风火担子,担子不轻啊!两年里,我们没出过什么事情,大人小孩都是平平安安,一个人进来,两个人出去。产妇等小孩一落地,就躺在床上,不要她动一动了,烧,洗,煮,弄大人,弄小孩,都是我们来,到出院的时候,一个个都长得胖胖的……”谭婶婶滔滔不绝地说着,荷妹不停地点着头。
“婶婶,这里有没有碰到过产妇不顺产的情况?”荷妹提问了。
“怎么没有,风险也就在这些事上,一看苗头不对,就得赶紧给医院打电话来救护车。”
“要是来不及呢?”
“打电话请医生来!”
“要是产妇产后发生变化呢?”
“打电话嘛!”
“婶婶,我们在哪里洗手呢?”荷妹忽然问。
“洗手?”谭婶婶不明白为什么忽然问这个,“洗手当然在脸盆里洗。”回答以后,她又辨了辨这问话的味道,心里又是一个不快。
“二丫头,这里不能和城里那些大医院比。”谭婶婶有些生气了,话也加重了分量。
“对!”荷妹一点也没觉出话里的责备意味,径自推窗开门,向外面张望起来。“婶婶,可有了办法了!”荷妹眉飞色舞地跳进来了,“婶婶,我们自己可以做土造自来水。人家托儿所都用自来水洗手了,我们产院里更需要这个。我看过了,井不远,只要墙上打一个洞……”
“荷妹,你刚来,还是看看再说吧!”说罢,谭婶婶就走进厨房,端消毒锅,封煤炉。
第一次见面,谭婶婶对荷妹的印象不能说好,但是要说坏,她也说不出坏在哪里,就是觉得不顺眼,不入调。
(选自《茹志鹃小说选》,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取材以小见大,作者没有一味歌颂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而是通过叙写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来表现普通人物的精神风貌。 |
| B.小说开头描绘了静谧的晚景,晚霞,竹篱,野花,组成一幅淡墨画,紧扣标题的“静静”,寥寥几笔交代了故事发生的环境。 |
| C.“径自推窗开门,向外面张望起来”“荷妹眉飞色舞地跳进来了”两句运用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表现了荷妹莽撞的性格。 |
| D.小说虽然写的是农村产院里发生的小事,但是却充分地展现了谭婶婶丰富的思想情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3.现代作家、翻译家冰心在评价《静静的产院》时说:这个短篇小说,结构是谨严的,没有一点废笔。请结合小说内容对此进行探讨。
相似题推荐
路标
茹志鹃
没有,没有,没有石子,没有草棍,没有树枝,更没有白粉,没有任何一点路标的痕迹。
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在这灰蒙蒙的天地当中,只有自己,站在一条灰蒙蒙的路上。
伍原想喊一声,就这么“喂”地喊一声。这里没有人,只是喊给自己听,壮壮胆,解解怯,泄泄闷,他要世界活着,自己活着。
但是,不能喊,不敢喊。他要窒息了。
行军路线是向北,他是向北走的。走了有三小时,也许四小时。走了四十里,也许是五十里。应该到铁路了,也许站在铁路的边边上了?
停住脚,沉住气。再看一看,再听一听,只要点点与人有关的东西,一缕烟,一个脚印,一丝灯光……那么,一切就有希望。自己,自己背上的档案,那里有埋在淮河畔的小榕的入党报告。还有老邹,咯着血的老邹,只有自己知道他躺在什么地方。
没有,一切与人有关的迹象都没有。
无声无息的泪水,乘着无月无星的夜,毫无顾忌地涌了出来。
“可能走岔了路?”伍原在心里跟自己商量着。
“不,方向是对的。在接近敌区时,是不做路标的。”
“那么,现在已经接近敌区了?”
“肯定,快到铁路了。”
“那就快走!不能停留。”顿时,伍原感觉在这灰蒙蒙的后面,有什么东西活动了起来,无数隐蔽的眼睛,冰冷的枪口,潜伏的危机。但是,往哪里走呢?
棉衣已经湿得贴在了胸口,背上是越来越沉的档案。伍原狠狠地跺了一脚,听天由命地坐到地上,泪水便像决了的堤。
可是,慢!这是什么?好像冥冥中有神,不,鬼!鬼火?
远远的,贴在地上,就那么一小点,一小点黄黄的光,不飘忽,不闪烁。伍原不敢眨眼,屏息静气,站起身,啊!一站起,它便像钻入了地下。伍原赶紧趴下。在呢!荧荧的,黄黄的,小小的一点。在呢!在呢!伍原小心翼翼地,敏捷地,他不知哪里来的这份力气,竞像只猫似的向那一小点轻盈迅速地爬去。
这如豆的一小点光。
世界再不是死的,自己再不是孤独的,部队就在前面,档案当然安然无恙交给指导员,老邹当然也会马上接回来。这一点如豆的光,明天,包含着一切的明天,这不飘忽,不闪烁,小如绿豆似的光。
有人了!找到人了!我到底找到老乡啦!“老乡!”伍原迫不及待地叫了一声。这一声叫,却不防把自己的眼泪叫得掉了下来。“老乡!老乡!”他连连地又叫了两声。一半是为了需要,一半是为了自己想叫。可是窝棚里静静地,没有任何反应。伍原赶紧爬到跟前,从高粱缝隙里看到,里面确确实实有一个人,一个老乡。他背对着棚口,席地坐着,正就着一盏油灯,低了头,紧张而有力地做着什么。
“老乡!”伍原稍稍放大了声音,那人依然低了头,急急地朝一个口袋里搓着玉米穗。看来,是一个聋子。伍原只得爬进棚去,正伸手想拉他一把,突然之间这聋子像背后长着触角,敏捷地跳起,把灯吹灭,然后转身想跑。伍原哪里肯让他跑掉,两臂一伸,把聋子的腿抱住了。那个人也不做声,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矮棚里,和伍原扭打起来。伍原不肯还手,一边抵挡着,一边死死抱住不放。明知他是个聋子,可还是大叫着:“老乡!老乡!”
“老乡!”却毫不理会,只是“唔唔”地叫着,挣出手来进行袭击。
伍原绝望了,这个人不但是聋子,还是个哑巴。伍原只得利用背上的重量,把他牢牢地揿在地上,但不知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自己是共产党,是野战军。伍原捉住哑巴的一只手,把它贴到自己帽子上,想让他明白,这不是国民党的大盖帽,这是八路军的帽子。可是哑巴并不理解,他死死捏紧拳头,硬勾着肘子,不肯就范,后来又忽然利用这个机会,迅速灵活地向伍原脸上猛击几下。
急,痛,头昏,眼前金星直冒,浑身大汗淋漓,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这一窘境。伍原突然觉得疲惫之极,手脚发软,不住地冒汗。却不知怎么,流下了眼泪,好像刚才在路上没来得及流下的泪水,却一齐奔涌而出。伍原伏在哑巴身上,大哭了起来,为自己,为前面走不完的路,为小榕,为老邹,也为这个倒霉而顽强的哑巴。
忽然,伍原觉得有只手,轻轻地摸索着自己的头,自己的帽子,自己的脸颊。哑巴顿时“哇哇”地大叫起来,那一只手还拍着伍原的肩,一边挣扎着要起来。伍原松了手,但说不清为什么,人却仍伏在地上抽抽噎噎。
哑巴挣脱了出来,忙忙地摸了火镰打着,点上了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伍原。猛然,他似乎省悟了什么,双手直向棚外挥动,又急急地拿起灯,拉着伍原爬出窝棚。他一手擎着灯,一手直指东北方向,然后做了个正步走的姿势,一双眼睛急切地盯着伍原。伍原点头,然后敬礼,然后回身走去。
伍原走上大路,回头望望,那一星豆子似的灯光,不飘忽,不移动,像是镶嵌在夜空当中。
夜空下的世界,依然斗转星移。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日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伍原是个迷路的八路军战士,为了把档案和掉队战友的消息送给部队,始终以坚定的信念毫不畏惧地前行。 |
| B.“老乡”虽是个哑巴,但内心明亮,在与伍原扭打后摸到他的军帽,知道了伍原的身份,并最终给了伍原帮助。 |
| C.小说以绿豆比喻荒野中的灯光,这灯光虽然微弱,但是它具有路标的作用,给了伍原力量、勇气和希望。 |
| D.小说前文通过描写“伍原感觉在这灰蒙蒙的后面,有什么东西活动了起来,无数隐蔽的眼睛,冰冷的枪口,潜伏的危机”,为后文遇到“老乡”埋下伏笔。 |
| A.小说多用短句,且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例如“不飘忽,不闪烁”出现两次,分别体现了伍原陷入困境的无助和快要走出困境的激动和欣喜。 |
| B.小说笔调简单朴实,没有波澜壮阔的场面,没有精细优美的语言,却刻画了一个小人物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 |
| C.茹志鹃的小说很有特点,本文与《百合花》一样情节相当曲折且善于用细节刻画人物内在特征,如写老乡“一手擎着灯,一手直指东北方向”。 |
| D.小说以《路标》为题,既关联着小说的故事情节,又有象征意味,蕴含了小说的主题,让读者思考。 |
4.小说三次写到伍原流泪,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请从展现人物心境的角度,谈谈你的理解。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
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摔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撩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惶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拼命忍住笑,随便地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在家时你干什么?”
“帮人拖毛竹。”
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
我又问:“你多大了?”
“十九。”
“参加革命几年了?”
“一年。”
“你怎么参加革命的?”我问到这里自己觉得这不像是谈话,倒有些像审讯。不过我还是禁不住地要问。
“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你还没娶媳妇吧?”
“……”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我还想问他有没有对象,但看到他这样子,只得把嘴里的话,又咽了下去。
两人闷坐了一会,他开始抬头看看天,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动身。
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地在用毛巾拭汗。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出了这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
我们到包扎所,已是下午两点钟了。这里离前沿有三里路,包扎所设在一个小学里,大小六个房子组成品字形,中间一块空地长了许多野草,显然,小学已有多时不开课了。我们到时屋里已有几个卫生员在弄着纱布棉花,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
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眼睛熬得通红,用一片硬拍纸插在额前的破毡帽下,低低地遮在眼睛前面挡光。
他一肩背枪,一肩挂了一杆秤;左手挎了一篮鸡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锅,呼哧呼哧的走来。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对我们又抱歉又诉苦,一边还喘息地喝着水,同时还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我只见他迅速地做着这一切。他说的什么我就没大听清。好像是说什么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去借。我问清了卫生员,原来因为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但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得向老百姓去借。哪怕有一二十条棉絮也好。我这时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也请了我那位同乡,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他踌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
我们先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他向东,我往西,分头去动员。不一会,我已写了三张借条出去,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心里十分高兴,正准备送回去再来借时,看见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怎么会没有借到呢?我有点惊奇地问。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响可不好。我叫他带我去看看。但他执拗地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他听了,果然就松松爽爽地带我走了。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的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地对我说道:“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我赶忙白了他一眼,不叫他再说。可是来不及了,那个媳妇抱了被子,已经在房门口了。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
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
我手里已捧满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没想到他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我只好开口叫他,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还没有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
刚走出门不远,就有人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妆。我听了,心里便有些过意不去,通讯员也皱起了眉,默默地看着手里的被子。我想他听了这样的话一定会有同感吧!果然,他一边走,一边跟我嘟哝起来了。
“我们不了解情况,把人家结婚被子也借来了,多不合适呀!……”我忍不住想给他开个玩笑,便故作严肃地说:“是呀!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零活,才积起了做被子的钱,或许她曾为了这条花被,睡不着觉呢。可是还有人骂她死封建。……”
他听到这里,突然站住脚,呆了一会,说:“那!……那我们送回去吧!”
“已经借来了,再送回去,倒叫她多心。”我看他那副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不知怎么的,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
他听我这么说,也似乎有理,考虑了一下,便下了决心似的说:“好,算了。用了给她好好洗洗。”他决定以后,就把我抱着的被子,统统抓过去,左一条、右一条的披挂在自己肩上,大踏步地走了。
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他回团部去。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的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
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现在,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
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打水,烧锅,作些零碎活。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她还是那样,笑眯眯的抿着嘴,偶然从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时不时的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后来她到底问我说:“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又抿了嘴笑着,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的分铺在门板上、桌子上(两张课桌拼起来,就是一张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地升起,好像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盏的汽油灯,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白夜”里来攻击,有多困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
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也憎恶起来了。
乡干部又来了,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我想到这里,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
……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
一会儿,我们的炮响了,天空划过几颗红色的信号弹,攻击开始了。不久,断断续续地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
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轻伤的问问,重伤的就得拉开他们的符号,或是翻看他们的衣襟。我拉开一个重彩号的符号时,“通讯员”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心跳起来。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号上写着×营的字样。啊!不是,我的同乡他是团部的通讯员。但我又莫名其妙地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
战斗开始后的几十分钟里,一切顺利,伤员一次次带下来的消息,都是我们突破第一道鹿砦,第二道铁丝网,占领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但到这里,消息忽然停顿了,下来的伤员,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在打。”或是“在街上巷战。”
但从他们满身泥泞,极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从那些似乎刚从泥里掘出来的担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战斗。
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耽搁下来。
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得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脸洗手,能吃得的喂他们吃一点,带着背包的,就给他们换一件干净衣裳,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
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
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
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1.小说中的通讯员有怎样的性格特点?请作简要分析。
2.小说是怎样塑造新媳妇这个人物形象的?请作简要分析。
3.小说标题是《百合花》,这个标题有怎样的意蕴?
4.小说的情节结构有着怎样的特点?
5.小说的叙述与描写,表现了怎样的语言风格?
6.这事一篇抒情性较强的小说,你认为小说在抒情上有何特色?
(甲)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
新媳妇却对我异样地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节选自《百合花》)
(乙)
我就问他说:“凡尼亚, 你的爸爸在哪儿啊?”他喃喃地说:“在前线牺牲了。”“那么妈妈呢?”“妈妈当我们来的时候给炸死在火车里了。”“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你在这儿没有一个亲人吗?”“没有一个。”“那你夜里睡在哪儿呢?”“走到哪儿,睡到哪儿。”
这时候,我的眼泪怎么也忍不住了。我就一下子打定主意:“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我要领他当儿子。”我的心立刻变得轻松和光明些了。我向他俯下身去,悄悄地问:“凡尼亚,你知道我是谁吗?”他几乎无声地问:“谁?”我又同样悄悄地说:“我是你的爸爸。”
天哪,这一说可说出什么事来啦!他扑在我的脖子上,吻着我的腮帮、嘴唇、前额,同时又像一只太平鸟一样,响亮而尖利地叫了起来,叫得连车厢都震动了:“爸爸!我的亲爸爸!我知道的!我知道你会找到我的!一定会找到的!我等了那么久,等你来找我!”他贴住我的身体,全身哆嗦,好像风下的一根小草。我的眼睛里蒙上了雾,我也全身打战,两手发抖……我当时居然没有放掉方向盘,真是奇怪极了!但我还是在无意间冲到水沟里,弄得马达也停了。在眼睛里雾没有消散以前,我不敢再开,怕撞在什么人身上。就这么停了约莫有五分钟,我的儿子一直紧紧地贴住我,全身哆嗦,一声不响,我用右手抱住他,轻轻地把他压在自己的胸口上,同时用左手掉转车子,回头向家里开去。我哪儿还顾得到什么谷仓呢?根本把它忘掉了。
(节选自《一个人的遭遇》)
1.甲文中加点的“瞟”和“瞪”可以互换吗?说明理由。2.两段选文一悲一喜,但同样有力地表达了故争主题,请从中各选一个相应的细节赏析。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静静的产院(节选)
茹志鹃
晚霞的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最后变成淡墨画似的几笔。公社产院外面的篱笆上,那些粉色的小花,也分不清朵数,形成模糊的一片,天色晚了。
谭婶婶挑满了一缸水,连气都没有歇一口,就忙着给两个休养的产妇做饭。在她这样的年纪,有这一份精力,这是她觉得自豪的。忙完了饭,她走到中间屋里来,伸手啪的一声扭亮了电灯,一霎时,这一间办公室兼产房立即变得那么宽敞高大起来,一切东西都好像放着光一样:产床上平展展的白单子,产床横头的白色屏风,白木的三屉桌,白的墙壁,白的屋顶……谭婶婶觉得奇怪,这些东西给电灯光一照,怎么就比平时白得多、漂亮得多呢!她眯起了眼睛,把这一切打量了又打量,同时想起昨天公社杜书记告诉她,养猪场场长张大嫂的二丫头荷妹,已在城里培训毕业,回来就派到产院里工作。产院增加了一个力量,产院飞快地在发展。谭婶婶心满意足地笑着,伸手啪的一声把灯扭熄。
“点灯不用油,不用油也得节省点用。”她重新点起玻璃罩的洋油灯,走去撬开煤炉,放上消毒锅,把一切要消毒的东西通通放进去煮。
“这不是跟医院差不多了吗?”谭婶婶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从自己三十九岁做寡妇想起,想到现在进产院……第二天,她起了一个大早,把自己脑后那个发髻剪掉了,短短的头发,杂着几根半白的发丝,显得又庄严又精神。大家见了她,也好像带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敬意。
在这里,在这所“跟医院差不多”的产院里,谭婶婶不但剪掉了发髻,她还学会了打针,打肌肉针、静脉针,学会了做产前检查,学会了量血压、抽血、缝线、拆线。每每碰到一些小手术,请镇上医生来动手术的时候,她就从从容容地做助手。对她的熟练沉着,医生也夸奖,甚至有的医生进一步要她自己学着动些小手术。谭婶婶笑笑,有些得意,同时这些医生把这产院要求得跟城里的医院一样,她又觉得好笑。谭婶婶对这一切都感到满意,不是没有道理的。
锅里的水嘶嘶地响了,谭婶婶心里翻腾了一阵,就望着电灯,恨不得立时来一个产妇,她真想在电灯光下面接生,就像在镇上,在城里的医院里一样:产妇躺在洁白的产床上,躺在雪亮的灯光下……
忽然啪的一声,电灯亮了,谭婶婶吓了一跳,回身一看,一个面孔黑黝黝的年轻姑娘,扛着行李,一手挟着一只氧气瓶,浑身热气腾腾地站在门口。
“婶婶,你不认识我啦!”那姑娘笑眯眯地站着没动。
“是二丫头!”谭婶婶跟二丫头的娘,还是做姑娘的时候就是好朋友,直到现在老姊妹俩还要好得很。
“婶婶,我派到这里来工作了。”荷妹回身坐下,就要谭婶婶介绍些产院的情况。“其实,差不多的情况你也都知道。这产院负责附近两个大队的产妇。跟我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个周嫂嫂,现在她害喜(指妇女怀孕初期种种感觉不舒适的反应),回家休息去了。产院成立这两年里,我们一共接了三百五十六个宝宝,还都顺顺当当。”谭婶婶一说到这些问题,不由得话就多了。三百五十六个,这可不是容易的啊!这要担多少风险。特别是产院还没有条件自己动手术,很多情况就得当机立断。该请医生的就请医生,该送医院的就送医院,差一点点就会坏事,所以谭婶婶说到这里,特别加重了语气:
“二丫头,这可是一副风火担子,担子不轻啊!两年里,我们没出过什么事情,大人小孩都是平平安安,一个人进来,两个人出去。产妇等小孩一落地,就躺在床上,不要她动一动了,烧,洗,煮,弄大人,弄小孩,都是我们来,到出院的时候,一个个都长得胖胖的……”谭婶婶滔滔不绝地说着,荷妹不停地点着头。
“婶婶,这里有没有碰到过产妇不顺产的情况?”荷妹提问了。
“怎么没有,风险也就在这些事上。一看苗头不对。就得赶紧给医院打电话来救护车。”
“要是来不及呢?”
“打电话请医生来!”
“要是产妇产后发生变化呢?”“打电话嘛!”
“婶婶,我们在哪里洗手呢?”荷妹忽然问。
“洗手?”谭婶婶不明白为什么忽然问这个。“洗手当然在脸盆里洗。”回答以后,她又辨了辨这问话的味道,心里又是一个不快。
“二丫头,这里不能和城里那些大医院比。”谭婶婶有些生气了,话也加重了分量。“对!”荷妹径自推窗开门,向外面张望起来。“婶婶,可有了办法了!”荷妹眉飞色舞地跳进来了,“婶婶,我们自己可以做土造自来水。人家托儿所都用自来水洗手了,我们产院里更需要这个。我看过了,井不远,只要墙上打一个洞……”
“荷妹,你刚来,还是看看再说吧!”说罢,谭婶婶就走进厨房,端消毒锅,封煤炉。
第一次见面,谭婶婶对荷妹的印象不能说好。但是要说坏,她也说不出坏在哪里,就是觉得不顺眼,不入调。
(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标题既指幽静的新生儿降生的地方,也喻指新事物、新思想悄悄诞生的地方,同时也暗示了小说的主旨。 |
| B.开篇部分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点——乡村的“产院”,渲染了宁静的气氛,也烘托出主人公此刻正陶醉在自己的事业已有成就之中的心理。 |
| C.电灯是一个道具,一面说明谭婶婶对产院现状的满足,一面引出荷妹的出场。 |
| D.通过荷妹来到产院后的心理、动作、语言描写,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她想改善产院用水卫生条件的急切、热情和果敢。 |
| A.《百合花》与本文均运用第三人称叙述故事,叙事生动,感染力强。 |
| B.小说讲述了谭婶婶与荷妹在产院第一次见面的情形,表现出二人在思想上的冲突: 一个对现状很满意,一个觉得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
| C.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写细腻、生动,在跟荷妹交流的过程中,谭婶婶心理上从“非常自豪”到最后“不置可否”。 |
| D.结尾的留白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将读者的思考引向深处,利于更好地表现小说的主旨。 |
4.有评论说“茹志鹃的短篇小说避重就轻地跳过宏大叙事,婉转着墨于时代大背景的间隙,于杯水微澜之处反映出时代特点”。请结合小说分析其创作的这一特点。
重返雪峰山
韩少功
三十多年前,我在怀化地区林业局挂职锻炼。这个局管辖全省的三分之一的山林,差不多是个山大王,不过也是个穷大王,我这个副局长下林区也得蹭货车,搭乘那种拉木头的解放牌或黄河牌,叮咚咣当响一路,尘土飞扬半遮天。
我因此认识了潘司机。
老潘胖,怕热,常冒油汗,入夏后多是光膀子上路,有时还把车门打开,找根木棍代替右脚顶住油门,半个身子探出车外兜一把风,呵嗬一声做鬼叫——那时的驾驶室里没空调,烤得人肉都有几分熟。
即便山道上人少车也少,这种野蛮操作还是吓我个半死。
我强迫他停车在路边,抽支烟,洗个冷水脸,嚼两块路边摊上的酸姜,休息片刻后再走。他嘟嘟囔囔,责怪我这纯粹是浪费时间。
我得承认,他开车并不误事,二十多年没出过事故,对雪峰山里的每条路都呼呼呼跑得顺溜。不论在哪里遇到路面塌方,走不成了,他也能在附近找到熟悉人家,高声大气,呼朋唤友,有吃有喝。
照他说,眼下有公路了,有汽车了,一天可以跑上几百里,已经是神行太保,是孙猴子一个筋斗腾云驾雾。要放在以前,雪峰山的几根木头要运出去,难呵,只能钻山缝、走水路,让人们先扎成小排,用的是藤条篾缆。驾着这种小排,由溪涧进入江河,进入资水或沅水那里的宽阔江面,才能把小排积攒成大排,上下叠加,前后左右串联,大若一座应浮游的人工岛,是可搭窝棚、架炉灶的那种,可捎带山货和数客的那种,以实现规模化经营。一声长啸报客往,他们迎山送岭,拨嶂推峰,顺流而下,一直漂到洞庭或长江那些大码头,把“人工岛”交付客商,这才算一次日落星沉的远行结束。作为雪峰山放出去的主要耳目,那年头日本军队何时撤了,汽车长成什么模样,城里女子 会不会勾魂……这些新鲜的重磅消息也总是由“排拐子”们带回山里,使一个个山塞不至于悠悠坠入历史之外的深远寂静。
我眼下见不到小排,连往日林区的简易公路也几乎看不到了。这次入山的邀访者姓陈,自称以前见过我,网上自我命名“哈协主席”——“哈” 就是湘语中傻的意思,二的意思。
在不少人看来,他确实有点傻和二——都什么年代了,不知打了什么鸡血,他从上市公司老总一路打拼成家乡的农民头,从繁华都市一鼓作气高歌猛进到穷山寨,所有的身家血本砸下去,居然在雪峰山多点开局,建起了五大景区,一心用沥青公路和过山缆车接通城乡,让山里的夕照、富氧、幽泉、古树、刺绣、柴门、篝火、美食、歌舞、梯田、先人传说、冬日的雪以及夏日的凉等,统统变成游客的幸福和山民的财富。这个“老土”,走村串户,大概想象大家都是同他一样喜欢大碗喝酒和大块吃肉,同他一样喜欢石头,喜欢木头,喜欢泥土和山脊线,喜欢开门见山和天高地阔,为此多年来不厌其烦地说服地方官员和合作伙伴。
难怪一些同事也笑:还真是个大哈呵。
这一次,我也想去听听他如何解说石头。时值深秋,雁阵南飞,高铁“复兴号”不知何时已从省城滑出,一路上静静地暗中加速,很快就有了时速近300公里的飞翔感。眼一眨过桥,眼一眨钻洞,眨一眼又是……整个行程几乎就是桥洞相连,上天入地反复切换,闹着玩儿似的,对沿途的山山水水压根儿就是粗枝大叶视若无物没心没肺,已把旅行简化成一条唰唰唰任性的直线,一种舒适和洁净的服务平均值,一种旅客们恍恍惚惚的科幻遭遇。我完全找不到感觉了。这还是雪峰山吗?喂,喂,这还是雪、峰、山吗?睁大眼睛朝窗外寻找,一匹匹翠绿翻阅过去,当年的“排拐子”们在哪里?当年潘师傅的简易公路和叮咚咣当尘土飞扬在哪里?而当时围着黄河牌大卡摸来摸去的一群娃娃中,一个挂着鼻涕的光屁股男孩,被汽车喇叭声吓一大跳的,莫非就是多年后的陈大哈?……
我突然有一点心酸,至少是心慌。
飞翔吧。飞翔。现代科技正在大大缩短空间距离,却也一再刷新世界图景,一步步放大了时间距离,如同电影在播放时突然提速,让往日的人和事速来速去,很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无踪影,退不可及更遇不可追。昨天已是久远。前天已是史前。我只能面对身后一片模糊,凭吊自己三十多年前的记忆残片——那是我青春的一部分。
也许,雪峰山,雪峰山,我这次完全算不上重返了,不过是奔赴一个重名的陌生之地,一片让人无措的茫然异乡,只能像一个两鬓斑白的婴儿,被山里的阳光刺得睁不开双眼,在那里经历新的一轮再生,一切都重新开始。
你飞翔吧——
我真不希望这样,但也希望就是这样。
(有删改)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本开头老潘开货车的细节,既写出了当时交通工具和道路的状况,也为后文老潘回忆“排拐子”做了铺垫。 |
| B.文章用“迎山送岭,拨嶂推峰”“日落星沉”等词句写曾经雪峰山的人出山不易,给人无限遐想,充满诗意。 |
| C.陈大哈这一人物,呈现出与常理相悖的一些状态,比如从老总到农民头,从繁华都市到贫穷村寨,明贬暗褒。 |
| D.文章在回忆雪峰山的一些人事时,语言幽默且口语化;写自己乘高铁重返雪峰山时却一改语言风格,令人触动。 |
3.文章结尾说“我真不希望这样,但也希望就是这样”包含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了悟禅师
凌鼎年
自了悟禅师到海天禅寺后,海天禅寺的平静就被打破了。
僧人们无论如何不明白,法眼方丈怎么会要求了悟禅师住下来,更不理解他为什么会容忍了悟的反常行为。
别的不说,这了悟自在海天禅寺住下后,竟从来没扫过一次地,从来没关过一次门。若轮到他值勤值夜,其他和尚总有些放心不下。
众僧都不甚喜欢这位新来的了悟禅师。所谓先进庙门三日大,比了悟先进庙门的,自认为比他有资历,也就不把了悟放在眼里,时不时斥责他,骂他是懒和尚。
了悟不气不恼,一笑了之。过了几天,众僧突然发现了悟在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为“空门岂用关”;下联为“净土何须扫”。
众僧看得呆了,一时竟无法驳斥了悟的这种奇谈怪论。有人去禀报了法眼方丈。法眼方丈闻听后,微微颔首,面露赞许之色。他传下话去:“了悟对禅的理解,已非你辈皮相之见,好好向他学道吧。”
僧人们都认为法眼方丈在偏护了悟,甚至认为他法眼有私,多少有些不服。
法眼方丈终于向众僧们说出了压在心底的一件事:那是半年前的一个黄昏,他匆匆赶回海天禅寺时,因山雨刚止,河水暴涨,木桥已被冲毁,有一年轻山姑为无法过河正发愁呢。法眼方丈见此,考虑再三,他卷起裤管,折一树枝,以树枝当手杖,一边探底,一边趟过了河。法眼方丈想:男女授受不亲,僧人戒色首先要远离女色,自己这样做,既给她做了示范,又不犯寺规,也算尽到普度众生之责了。然而,那位山姑不知是没有领会法眼方丈的暗示,还是胆小,依然站在河对岸干着急。天渐渐暗下来了,一个山姑过不了河,那如何是好?正在这时,走来一其貌不扬的和尚,和尚上前向山姑施礼后,就抱着山姑过了河,和尚把山姑放下地后,满脸通红的山姑一脸羞涩地向和尚道了谢。和尚说了声:“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就一声不响地继续赶路了。
法眼方丈忍不住上前问:“这位和尚,出家人应不近女色,你怎可抱一个姑娘呢?”那和尚哈哈大笑说:“我早把那姑娘放下了。你怎么反而老放不下呢?”法眼闻之大惭,始悟遇到得道高僧了,就极力邀请了悟禅师到海天禅寺住下。
这件事对法眼方丈震动很大,他深感了悟禅师道行深厚,有心好好观察,让之熟悉海天禅寺后,再作打算。
不久,清兵南下,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烈之事,善男信女逃难的逃难,避灾的避灾,寺庙的香火一下冷落了许多。
海天禅寺落入清兵之手是早晚的事,胆小的僧人离寺避到了乡下,了悟却天天在大殿念经打坐,仿佛不知大军压境之事。
一个阴霾之天,清军一位大胡子将军率军士冲进了寺庙,其他僧人全逃了,唯了悟禅师依然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念他的经,对大胡子将军的到来不管不顾,大胡子将军见这和尚竟敢如此蔑视自己,气不打一处来,厉声喝问:“好大的胆子,竟敢如此目无本将军,你知道不知道本将军杀人如刈草一般!”
了悟正眼也没瞧大胡子将军一眼,朗声回答说:“将军你大概还不知道寺庙中也有不惧死的和尚吧,既然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本来大胡子将军想大开杀戒,烧了寺庙,但听了了悟的回答,又从心底里佩服这位和尚的豪气与胆识,遂下令撤退。
海天禅寺就这样免于兵灾。
法眼方丈因此有了把方丈之位传给了悟的念头,了悟闻知后借口自己乃闲云野鹤,执意谢绝了法眼方丈的美意,终于又云游四海去了。
临走时,他留下一偈语:泥佛不渡水,金佛不渡炉,木佛不渡火,真佛内里坐。遂头也不回地走了。
法眼方丈与众僧们都默默念着这偈语,各人参悟着。
(选自《微型小说精选》,有删改)
1.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理解,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作者采用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手法,综合运用了神态、动作、语言等细节描写刻画了了悟禅师。 |
| B.了悟背村姑过河这件事征服了法眼和众和尚,也为征服大胡子将军做了铺垫,也与开头一脉相承,同时使情节合理不突兀。 |
| C.了悟禅师在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为“空门岂用关”,下联为“净土何须扫”这其实是故弄玄虚,为自己的偷懒找借口。 |
| D.方丈第一次遇到了悟禅师,见识了他的深厚的道行后,就产生了把方丈之位传给他的想法。 |
3.对结尾处的偈语你有怎样的参悟?请结合文本加以解读。
暮色中的炊烟
迟子建
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飘渺。无云的天气中,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而有云的日子,它们就是云的长裙下飘逸着的流苏。
女人们喜欢在晚饭后串门,她们去谁家串门前,要习惯地看一眼这家烟囱冒出的炊烟,如果它格外地浓郁,说明人家的晚饭正忙在高潮,饭菜还没有上桌呢,就要晚一些过去;而如果那炊烟细若游丝、若有若无,说明饭已经吃完了,你这时过去,人家才有空儿聊天。炊烟无形中充当了密探的角色。
炊烟总是上升的,它的气息天空是最为熟悉的了。这气息,常让我忆起一个与炊烟有关的老女人的命运。
这是个俄罗斯老太太,我们都叫她“老毛子”。她是斯大林时代避难过来的,早已加入了中国国籍。北极村与她的祖国,只是一江之隔。所以每天我从东窗看见的山峦,都是俄罗斯的。她嫁了个中国农民,是个马夫,生了两个儿子。她的丈夫死后,两个儿子相继结了婚,一个到外地去了,另一个仍留在北极村,不过不跟她住在一起。那个在北极村的儿子为她添了个孙子,叫秋生。秋生呆头呆脑的,他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见了人只是笑,不爱说话,就是偶尔跟人说话也是说不连贯。秋生不像他的父母很少登老毛子的门,他三天两头就来看望他的奶奶。秋生一来就是干活,挑着桶去水井,一担一担地挑水,把大缸小缸都盛满水;再抡起斧子劈柴火,将它们码到柴垛上;要不就是握着扫帚扫院子,将屋前屋后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所以我从东窗,常能看见秋生的影子。除了他,老毛子那里再没别人去了。
那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苏联的巡逻机常常嗡嗡叫着低空盘旋,我方的巡逻艇也常在黑龙江上徘徊。不过两国的百姓却是友好的,我们到江边洗衣服或是捕鱼,如果看见界河那侧的江面上有小船驶过,而那船头又站着人的话,他们就会和我们招手,我们也会和他们招手。
那时村中的人很忌讳和她来往。她似乎也不喜欢与村中人交往,从不离开院门,只呆在家里和菜园中。我到玉米地时,隔着栅栏,常能看见她在菜园劳作的身影。她个子很高,虽然年纪大了,但一点也不驼背。她喜欢穿一条黑色的曳地长裙,戴一条古铜色三角巾。她的皮肤非常白皙,眼窝深深凹陷,那双碧蓝的眼睛看人时非常清澈。我姥姥不喜欢我和她说话,但有两次隔着栅栏她吆喝我去她家玩,我就跃过栅栏,跟着她去了。我至今记得她的居室非常整洁,北墙上悬挂着一个座钟,座钟下面是一张紫檀色长条桌,桌上喜欢摆着两个碟子,一只装着蚕豆,一只装着葵花子,此外还有一个茶壶、一个茶盅和一副扑克牌。这些东西展现了她家居生活的情态,喝茶,吃蚕豆,嗑瓜子,摆扑克牌。她的汉语说得有些生硬,好像她咬着舌头在说话。她把我领到家后,喜欢把我抱起,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的时候,她就为我抓吃的去了。蚕豆、瓜子是最常吃的,有的时候也会有一块糖。我自幼满口虫牙,硬东西不敢碰,而她虽然已是个老人,牙齿却格外地坚实,嚼起蚕豆有声有色的,非常轻松和惬意。与她熟了后,她就教我跳舞,她喜欢站在屋子中央,扬起胳膊,口中哼唱着什么,原地旋转着。她旋转的时候那条黑色的裙子就鼓胀起来了,有如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北极村的很多老太太都缠过足,走路扭扭摆摆的,且都是小碎步;而老毛子却是个大脚片子,她走起路来又稳又快,我那时把她爱跳舞归结为她拥有一双自由的脚,并不知道一双脚的灵魂其实是在心上。
那些不上她家串门的邻居,其实对老毛子也是关心的。他们从两个途径关心着她,一个是秋生,一个就是炊烟了。人们见了秋生会问他,秋生,你奶奶身体好吗?秋生嘿嘿地笑,人们就知道老毛子是硬朗的。而我姥姥更喜欢从老毛子家的烟囱观察她的生活状况,那炊烟总是按时按晌地从屋顶升起,说明她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很有规律。大家也就很放心。
冬天到来的时候,园田就被白雪覆盖了。天冷,我就很少到老毛子家去玩了。玻璃窗上总是蒙着霜花,一派朦胧,所以也很少透过东窗去看那座木刻楞房屋了。她家的炊烟几时升起,又几时落下,我们也就不知晓了。
老毛子在冬季时静悄悄地死了,她是孤独地离开这个冰雪世界的。那几天秋生没过来,人们是通过她家的烟囱感觉她出了事的。住在她家后一趟房的人家,每天早晚抱柴生火时,总要习惯地看一眼老毛子的烟囱,结果她连续两天都没有发现那烟囱冒出一缕炊烟,知道老毛子大事不好了,于是喊来她的家人,进屋一看,老毛子果然已经僵直在炕上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暮色苍茫的时分看到过那幢房屋飘出炊烟,尽管村子里其它房屋的炊烟仍然妖娆地升起,但我总觉得最美的一缕已经消逝了。
1.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开头一段,不仅写出了炊烟的特征,而且还给读者传递了独特的信息,为下文有关内容的展开作铺垫。 |
| B.文章说“我那时把她爱跳舞归结为她拥有一双自由的脚,并不知道一双脚的灵魂其实是在心上”,这句话体现了老太太对待生活的态度。 |
| C.“她似乎也不喜欢与村中人交往,从不离开院门,只呆在家里和菜园中。”这体现了俄罗斯老太太的孤独冷漠。 |
| D.文章结尾作者说俄罗斯老太太的炊烟最美,寄寓了对老人的怀念和赞美,深化了文章的主题,也给读者留下回味的余地。 |
| A.文章综合运用了记叙、描写、抒情等表达方式,讲述了一个与生活在北极村的俄罗斯老太太有关的故事。 |
| B.这篇文章艺术手法灵活而多样,如“她旋转的时候那条黑色的裙子就鼓胀起来,有如一朵盛开的牵牛花”使用了比喻修辞,形象生动。 |
| C.“这气息,常让我忆起一个与炊烟有关的老女人的命运。”这句话将文章内容由景物描写过渡到对老太太的回忆。 |
| D.作品中北极村村民是温暖的,但是也是谨慎的,选文将村民和老太太进行对比,展现了当地的风俗、人情,有利于表现主题。 |
4.文章以“暮色中的炊烟”为题有什么好处?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
抱 孙
老舍
难怪王老太太盼孙子呀;不为抱孙子,娶儿媳妇干吗?也不能怪儿媳妇成天着急;本来嘛,不是不努力生养呀,可是生下来不活,或是不活着生下来,有什么法儿呢!就拿头一胎说吧:自从一有孕,王老太太就禁止儿媳妇有任何操作,夜里睡觉都不许翻身。哪里知道,到了五个多月,儿媳妇大概是因为多眨巴了两次眼睛,小产了!难道这还算不小心?哼,他竟自死了。命该如此!
现在,王少奶奶又有了喜,肚子大得惊人,看着颇象轧马路的石碾。看着这个肚子,王老太太心里仿佛长出两只小手,成天抓弄得自己怪要发笑的。王老太太可不只是祷告烧香呀,儿媳要吃活人脑子,老太太也不驳回。半夜三更还给儿媳妇送肘子汤,鸡丝挂面……儿媳妇呢,点心就能吃二斤翻毛月饼:吃得顺着枕头往下流油,被窝的深处能扫出一大碗什锦来。孕妇不多吃怎么生胖小子呢?婆婆、儿媳、娘家妈对于此点都完全同意。
收生婆已经守了七天七夜,压根儿生不下来。偏方儿,丸药,子孙娘娘的香灰,吃多了;全不灵验。
到第八天头上,少奶奶疼得满地打滚。王老太太急得给子孙娘娘跪了一股香,娘家妈把天仙庵的尼姑接来念催生咒;还是不中用。收生婆施展了绝技,却一无成绩。
有人说,少奶奶得上医院。王老太不同意。洋鬼子,二毛子,懂什么;王家要“养”下来的孙子,不要“掏“出来的。娘家妈也发了言,催生咒还没念完,忙什么?不敬尼姑就是看不起神仙!又耗了一点钟,少奶奶直翻白眼。王老太太眼中含着老泪,心中打定了主意:保小的不保大人。媳妇死了,再一个;孩子更要紧。她翻白眼呀,正好一狠心把孩子拉出来。告诉了收生婆,拉!娘家妈可不干了呢,孙子算老几,女儿是女儿。上医院吧。
一到医院,王老太太就炸了烟。还得挂号?生孩子又不是买官米,给钱就结了,挂哪门子号,你当我的孙子是封信呢!咳,为孙子,忍了。
医生来了。一见面,王老太太就炸了烟,男大夫!男医生当收生婆?我的儿媳妇不能叫男子汉给接生。这一阵还没炸完,又出来两个大汉,抬起儿媳妇就往床上放。
老太太连耳朵都哆嗦开了!这是要造反呀,人家一个年青青的孕妇,怎么一群大汉来动手脚的?“放下,你们这儿有懂人事的没有?要是有的话,叫几个女的来,不然,我们走!恰巧遇上个顶和气的医生,他发了话:“放下,叫她们走吧!”
王老太太咽了口凉气,咽下去砸得心中怪热的,要不是为孙子,至少得打大夫几个最响的嘴巴。县官不如现管,谁叫孙子故意闹脾气呢。抬吧,不用说废话。
果不出王老太太所料,得用手术。手要是竖起来,还不是开刀问斩?大夫说:孩子太大,用手术,大人小孩或者都能保全。不然,全有生命的危险。王老太太一个字没听见。掏是行不开的。“那么你不要孙子了?”果然有效。
等了不晓得多大的时候,眼看就天亮了,才掏了出来,好大的孙子,足分量十三磅!王老太太不晓得怎么笑好了,拉住亲家母的手一边笑一边刷刷的落泪。亲家母已不是仇人了,变成了老姐姐。大夫也不是二毛子了,是王家的恩人,恨不得马上赏给他一百块钱。
好容易看见大夫出来了。王老太就要求媳妇和孙子出院,理由是头胎孙子要办三日宴,医生不同意,再三相劝无效后,怒道“莫非三日宴比人命重要”?
王老太确是以为办三天比人命要紧,可不便于说出来,因为娘家妈在旁边听着呢。“叫她躺着招待客人,不必起来就是了。大夫还是不答应,“你自己看看去,她能走不能?”
儿媳妇在床上放着的一张卧椅上躺着呢,脸就象一张白纸。娘家妈哭得放了声,王老太太到底心硬,只落了一半个泪,紧跟着炸了烟:“怎么不叫她平平正正的躺下呢?直着呀,肚子上缝的线就绷了。”大夫说。“那么不会用胶粘上点吗?”王老太太总觉得大夫没有什么高明主意。好吧。先把孙子抱走。“头大的孙子,洗三不请客办事,还有什么脸活着?
到底把孙子抱出来了。王老太太抱着孙子上了汽车,一上车就打喷,一直打到家,每个喷都是照准了孙子的脸射去的。到了家,赶紧派人去找奶妈子,孙子还在怀中抱着,以便接收嚏喷。
不错,王老太太知道自己是着了凉;可是至死也不能放下孙子。到了晌午,孙子接了至少有二百多个嚏喷,身上慢慢的热起来。王老太太更不肯撒手了。到了下午三点来钟,孙子烧得象块火炭了。到了夜里,奶妈子已雇妥了两个。可是孙子死了,一口奶也没有吃。
王老太太只哭了一大阵;哭完了,她的老眼瞪圆了:“掏出来的!掏出来的能活吗?跟医院打官司!那么沉重的孙子会只活了一天,哪有的事?全是医院的坏,二毛子们!”
(摘编自老舍《抱孙》写于1938年,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第一段中,王老太太将抱孙愿望的屡次落空归结于“命该如此”,这既表现了她想抱孙而不得的无奈,也为她在产子风波中的行为、态度做出铺垫。 |
| B.在本次孕产事件中,医生的处置科学合理、充满智慧,但最终孩子死了,医生自己也可能惹来官司,如此安排,寄寓了作者深切的悲哀和愤慨。 |
| C.小说用喜剧的笔法写悲剧,营造出一种“笑中带泪”的艺术效果,这可以淡化悲剧意义,使作品不至于“赶尽杀绝”,体现出老舍的宽厚和同情。 |
| D.老舍善于选取生活中的典型事件,组织成悲喜更迭的曲折情节,本文既有对当时社会观念的讽刺,也能引起读者对当今一些社会现象的反思。 |
| A.“不为抱孙子,娶儿媳妇干吗”,文章第一句话就点出了以王老太太为代表的旧社会对女人的看法。 |
| B.为了能够抱上孙子,王老太太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不仅送肘子汤、鸡丝挂面,而且不允许儿媳妇睡觉时翻身、多眨巴眼睛。 |
| C.“孙子接了至少有二百多个嚏喷……可是孙子死了”,此部分文本表现了爱孙如命的王老太太因为自己的“不讲卫生、育儿观念落后”导致了“孙子”的死亡。 |
| D.“掏出来的!掏出来的能活吗?……那么沉重的孙子会只活了一天,哪有的事?”此处说明了以王老太太为代表的国人到了20世纪依旧盲目排斥科学的可悲情状。 |
4.老舍的作品以充满喜剧性著称,请以本文为例,分析其喜剧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永不掉队
[苏联]奥•冈察尔
高罗沃依在学院里一眼就认出了葛洛巴,但他没能立刻拿定主意去见失明的副教授。每逢在通道或是在教室里遇见他时,这位军官总觉得自己有些过意不去。不知为什么,高罗沃依至今还记得行军中那件遥远的往事。但他同时也感到骄傲,因为他曾指挥过这样的人。
是的,1941年是一种战线,现在是另一种战线了。如今,在高罗沃依面前站着的是他从前指挥过的一个士兵,这个人站在新的讲台上,高昂着头活像一位统帅。教室里的学员们认真领会着他讲的每个字。
领会是不容易的。高罗沃依有时觉得他掌握不了这一切。他努力再努力,但还是落在后面。他根本没有想到过理论物理有时他觉得这已是力所不及的了。有时也想拂袖而去,另寻其他职业。
他和葛洛巴已经谈过几次话了,然而副教授一次也没有提到过那久远的往事,连这样的暗示也没有。“他也许忘记了?”高罗沃依时而这样想。
有一次,高罗沃依和同班的少女们到葛洛巴家里去请教。副教授依着习惯,反问起她们来,考查她们掌握的程度。他挺着腰板坐在桌旁,精神抖擞,穿着一身黑制服,和平常一样,纽扣扣得整整齐齐。那带有伤疤的面孔不时抽搐着。
葛洛巴询问的那个少女没能答上来。他又问了第二个人,还是没有答上来。
“那么您呢,高罗沃依?”
老师耐心而客气地继续问道:“您也许能解答?”
高罗沃依涨红了脸,站了起来。
“我试试看。”
其实,他对这个问题也说不清,可是让他对老师说“不会”,又说不出口。
副教授的脸闪出了光辉,他很满意。他虽然看不见自己从前的那位身材匀称、受过严格训练的连长,可是看他那样子,他在众人面前也以他有过这个学生而感到骄傲。
高罗沃依心里很紧张,他回答时说错了,又说了一遍。副教授耐心地听着。高罗沃依越说越觉得自己是在胡诌乱讲……最后,高罗沃依生气地把手一甩:
“完了。”
老师感到不安。
“高罗沃依同志,什么完了?”
“我不念了!……够了,我要离开学院!”
“您说什么,高罗沃依?您再重复一遍。”
“我耽误了四年,问题就在这里。如今如今我赶不上了。”
“您赶不上了?”副教授提高了嗓门。“您这是认真说的话吗?”
少女们提心吊胆地窃窃私语。
“请你们先出去!出去一会儿。”副教授对她们喊了一句。
当女大学生们消逝在门外后,葛洛巴非常激动地对高罗沃依说道:
“您打算另找一条容易走的路?这条路太艰难?力不胜任?可是您还记得吗?……”
高罗沃依感到葛洛巴现在会提起那遥远的往事。
葛洛巴真的说了:
“您还记得在草原上那可怕的一夜吗?”
“您还记得我是怎样掉了队,您是怎样对待我……”
“您还记得当时您说的话吗?‘没听见……聋啦……总得为您负责……’那时您教我懂得了许多道理,高罗沃依同志。最初我感到非常委屈,但是后来后来我想起您时,我看到了您的品德,您的做法是对的。过去您在祖国面前为我们战士们负责。如今,依照祖国的意愿,我们彼此调换了一下位置。难道我现在不为高罗沃依负责吗?难道说,他——我过去的指挥员——要掉队,要放弃学业,要寻找一个轻而易得的饭碗,我就不痛心吗?请您告诉我,我应该把您这种行为叫做什么?”
高罗沃依笔直地站在副教授面前,一声不响。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安排的,”副教授稍微镇静了一些,继续说:“让我们永远彼此互相负责吧。在某一个阶段您为我负责,在另一个阶段——我就为您负责。那时您对我喊道……‘大步追上去!’是这样吧?”
“是的。”高罗沃依喃喃地说。
“这样就帮助了我。还帮助我经受了更多的考验。”
“当时容易些。”
“完成了的事,总会觉得容易些。”副教授认真地说下去,“我本不打算向您提起这件事,请您不要以为我是个爱记仇的人。”
“我没有这样认为。”高罗沃依说。他确实也没有这样想。
“好吧,让我再也不要听见类似的话了。”副教授半开玩笑地说,“什么不念了,不干了,把这些都忘掉!”
“是。”
“连队向物理进军了。是的,向物理进军。所以您,高罗沃依同志,必须赶上。”
高罗沃依脸上露出了微笑。
“我一定追上去。”
“去吧!”
高罗沃依低头观察自己过去的战士,心里想:“他真有指挥员的气魄。”
(有删节)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1941年是一种战线,现在是另一种战线了”,暗示小说故事以二战结束苏联恢复建设为背景,其中“战线”一词还带着那个特定时代的气息。 |
| B.小说行文中三次提及那件遥远的往事,表明这件往事在高罗沃依见到副教授后一直萦绕在他心间,这样写起到了制造悬念、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
| C.小说写高罗沃依和同班少女们到副教授家请教,为高罗沃依和副教授矛盾的展开创设了环境,给人生活真实感,有助于刻画主要人物的形象。 |
| D.结尾写“他真有指挥员的气魄”与开篇“高昂着头活像一位统帅”形成照应,措辞的变化,写出了高罗沃依对副教授由不信服到折服的变化。 |
3.“永不掉队”体现了一种精神。请结合文本谈谈你对这种精神内涵的理解。
文本一:
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注]
朱光潜
在当代画家中,我认识丰子恺先生最早,也最清楚。说起来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他和我都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他在湖边盖了一座极简单而亦极整洁的平屋。同事夏丐尊、朱佩弦、刘薰宇诸人和我都和子恺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块聚会。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后来我们都离开白马湖,在上海同办立达学园。大家挤住在一条僻窄而又不大干净的小巷里。学校初办,我们奔走筹备,都显得很忙碌,子恺仍是那副雍容恬静的样子,而事情却不比旁人做得少。虽然由山林搬到城市,生活比较紧张而窘迫,我们还保持着嚼豆腐干花生米吃酒的习惯。酒后有时子恺高兴起来了,就拈一张纸作几笔漫画,画后自己木刻,画和刻都在片时中完成,我们传看,心中各自欢喜,也不多加评语,在文艺中领取乐趣。
当时的朋友中浙江人居多,那一批浙江朋友们都有一股清气,即日常生活也别有一般趣味,却不像普通文人风雅相高。子恺于“清”字之外又加一个“和”字。他的儿女环坐一室,时有憨态,他见着居然微笑;他自己画成一幅画,刻成一块木刻,拿着看看,欣然微笑;在人生世相中他偶然遇见一件有趣的事,他也还是欣然微笑。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黄山谷尝称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我的朋友中只有子恺庶几有这种气象。
当时一般朋友中有一个不常现身而人人都感到他的影响的——弘一法师。他是子恺的先生。在许多地方,子恺都得益于这位老师。他的音乐图画文学书法的趣味,他的品格风采都颇近于弘一。在我初认识他时,他就已随弘一信持佛法。不过他始终没有出家,他不忍离开他的家庭。他通常吃素,不过做客时怕给人家添麻烦,也随人吃肉边菜。他的言动举止都自然圆融,毫无拘束勉强。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能了解佛家精神的人。他的性情向来深挚,待人无论尊卑大小,一律蔼然可亲,也偶露侠义风味。弘一法师近来圆寂,他不远千里,亲自到嘉定来,请马蠲叟先生替他老师作传。
我对于子恺的人品说这么多的话,因为要了解他的画品,必先了解他的人品。一个人须先是一个艺术家,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都是艺术的。他的作品有一点与时下一般画家不同的,就是他有至性深情的流露。子恺本来习过西画,在中国他最早作木刻,这两点对于他的作风都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这些只是浮面的形象,他的基本精神还是中国的,或者说,东方的。我知道他尝玩味前人诗词,但是我不尝看见他临摹中国旧画。他的底本大半是实际人生一片段,他看得准,察觉其中情趣,立时铺纸挥毫,一挥而就。他的题材变化极多,可是每一幅都有一点令人永久不忘的东西。我二十年前看过他的一些画稿——例如《指冷玉笙寒》《月上柳梢头》,到于今脑里还有很清晰的印象。他的画里有诗意,有谐趣,有悲天悯人的意味;它有时使你悠然物外,有时使你置身市尘,也有时使你啼笑皆非,肃然起敬。他的人物装饰都是现代的,没有模拟古画仅得其形似的呆板气,可是他的境界与粗劣的现实始终维持着适当的距离。他的画极家常,造境着笔都不求奇特古怪,却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他的画就像他的人。
书画在中国本有同源之说。子恺在书法上曾经下过很久的功夫。时下一般画家的毛病就在墨不入纸,画挂起来看时,好像是飘浮在纸上,没有生根;他们自以为超逸空灵,其实是画家所谓“败笔”,像患虚症的人的浮脉,是生命力微弱的征候。子恺的画却没有这种毛病。他用笔尽管疾如飘风,而笔笔稳重沉着,像箭头钉入坚石似的。在这方面,我想他得力于他的性格,他的木刻训练和他在书法上所下的功夫。
文本二:
文学艺术作品绝对要有真情,有真情才能产生诗意。现在有些散文似乎蛮有诗意,但那不是真正的诗意。如有些诗一样,有些诗每一句似乎都有诗意,但通篇读完后,味似嚼蜡,它是先有一两个好句子然后衍变成诗的。而有些诗每一句都平白如话,但整体却留给了我们东西,这才真正称作诗。我害怕那些表面诗意的浮华的散文。现在人写东西,多是为写东西而写东西,为发表而发表,这是我们现在作品多但好作品少的一个原因。试想想,你有多少诗意要发,有多少情要感慨?其实许多作者并不是专门写散文的,他们在做别的学问的过程中偶尔为之,倒写成了传世的散文之作。说到趣味,散文要写得有趣味当然有形式方面的、语言方面的、节奏方面的许多原因,但还有一点,这些人会说闲话。我称之为闲话,是他们在写作时常常把一件事说清楚之后又说些对主题可有可无的话,但是,这些话恰恰增加了文章的趣味。
(节选自贾平凹《我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
【注】朱光潜(1897-1986),当代著名美学家,文本一《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为作者为嘉定丰子恺画展所作。
1.下列对文本一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丰子恺兴之所至提笔作画,体现出他高超的技艺,同时也让朋友们感受到文艺中的真正乐趣。 |
| B.丰子恺的画作平易深刻,用笔沉着,深受人们喜爱,这得益于他的性格和他深厚的艺术功底。 |
| C.这篇散文通过介绍丰子恺的人品进而让人了解其画品,作者赞美他是基于其画展宣传的需要。 |
| D.这篇散文通过对丰子恺的神态、行为等特征的描绘,展现出了一个人品与画品统一的画家形象。 |
| A.朱自清,现代散文家、诗人、民主战士,具有民族气节。和丰子恺的画一样,朱自清的散文也充满了诗意。 |
| B.黄山谷即黄庭坚,“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形容一个人的个性如春风般和煦,借此意在赞美丰子恺雍容恬静。 |
| C.“月上柳梢头”是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中的句子,描绘的是八月十五中秋节赏灯时年轻人约会的情景。 |
| D.文中所写诸人,热爱文艺,情趣高雅,虽然性格各异,却有“竹林七贤”那种不羁的性格特征,颇具魏晋风骨。 |
4.某中学组织学习名家优秀散文,欲对《丰子恺的人品与画品》进行评论,请结合两则文本,列出评论要点。